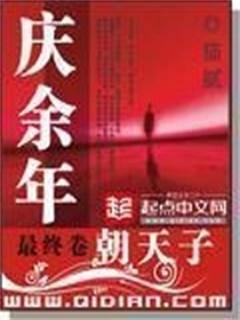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楔子 壹塊黑布
- [ 免費 ] 第壹章 故事會
- [ 免費 ] 第二章 無名黃書
- [ 免費 ] 第三章 練功與讀書
- [ 免費 ] 第四章 深夜來客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悶枕
- [ 免費 ] 第六章 來者是客
- [ 免費 ] 第七章 墳場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年齡不是問題
- [ 免費 ] 第九章 不恥而問
- [ 免費 ] 第十章 第五宗師?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霸道之氣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簡單粗暴的解釋 ...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誰是販鹽的老辛? ...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暫別費介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京都來信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我把菜刀獻給妳 ...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血淚的繼續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臉面問題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站在高崗上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痛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 騷客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 貓扣子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三章 刺客
- [ 免費 ] 第二十四章 豆腐如玉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五章 蓋羊毛毯的老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六章 監察院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七章 紅袖添香夜抄書 ...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八章 書賊
- [ 免費 ] 第二十九章 往事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 有歌者來
- [ 免費 ] 第三十壹章 傾船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二章 閑年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三章 竹帥
- [ 免費 ] 第三十四章 雨夜回憶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五章 慶歷四年春 ...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六章 去京都?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七章 前夜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八章 離開淡州
- [ 免費 ] 第三十九章 望京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 初入範府
- [ 免費 ] 第四十壹章 柳氏
- [ 免費 ] 第四十二章 若若的釋名 ...
- [ 免費 ] 第四十三章 父子
- [ 免費 ] 第四十四章 宮中秘辛
- [ 免費 ] 第四十五章 他鄉遇故知 ...
- [ 免費 ] 第四十六章 紅寶書
- [ 免費 ] 第四十七章 地攤文學
- [ 免費 ] 第四十八章 在酒樓上
- [ 免費 ] 第四十九章 什麽叫風骨? ...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 靖王世子
- [ 免費 ] 第五十壹章 馬車上
- [ 免費 ] 第五十二章 獨行
- [ 免費 ] 第五十三章 監察院內外 ...
- [ 免費 ] 第五十四章 糖葫蘆與慶廟 ...
- [ 免費 ] 第五十五章 貴人
- [ 免費 ] 第五十六章 心動
- [ 免費 ] 第五十七章 緣來是她
- [ 免費 ] 第五十八章 算帳少年
- [ 免費 ] 第五十九章 兄妹閑敘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 計劃書
- [ 免費 ] 第六十壹章 早夏
- [ 免費 ] 第六十二章 簡單的理由 ...
- [ 免費 ] 第六十三章 初吟
- [ 免費 ] 第六十四章 王府
- [ 免費 ] 第六十五章 又遇郭保坤 ...
- [ 免費 ] 第六十六章 湖那邊
- [ 免費 ] 第六十七章 出詩打人第壹記 ...
- [ 免費 ] 第六十八章 拋詩砸人
- [ 免費 ] 第六十九章 靖王發話
- [ 免費 ] 第七十章 司理理
- [ 免費 ] 第七十壹章 如蘭
- [ 免費 ] 第七十二章 麻袋之痛
- [ 免費 ] 第七十三章 官司臨頭
- [ 免費 ] 第七十四章 公堂內外的相聲 ...
- [ 免費 ] 第七十五章 訟
- [ 免費 ] 第七十六章 宮中
- [ 免費 ] 第七十七章 耳光
- [ 免費 ] 第七十八章 太後聖明
- [ 免費 ] 第七十九章 探未婚妻去 ...
- [ 免費 ] 第八十章 登堂
- [ 免費 ] 第八十壹章 入室
- [ 免費 ] 第八十二章 破窗
- [ 免費 ] 第八十三章 交錯時光的愛戀 ...
- [ 免費 ] 第八十四章 族學
- [ 免費 ] 第八十五章 慶余堂的葉掌櫃 ...
- [ 免費 ] 第八十六章 夫妻夜話
- [ 免費 ] 第八十七章 螞蟻上樹? ...
- [ 免費 ] 第八十八章 牛欄街少年殺人事 ...
- [ 免費 ] 第八十九章 調查
- [ 免費 ] 第九十章 範閑在行動
- [ 免費 ] 第九十壹章 王啟年的人生 ...
- [ 免費 ] 第九十二章 滄州城外話京都 ...
- [ 免費 ] 第九十三章 協律郎獨占花魁 ...
- [ 免費 ] 第九十四章 偷香不誤賣書功 ...
- [ 免費 ] 第九十五章 淡泊書局
- [ 免費 ] 第九十六章 參將自殺
- [ 免費 ] 第九十七章 天牢欺弱女 ...
- [ 免費 ] 第九十八章 言辭若香
- [ 免費 ] 第九十九章 葡萄架倒了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章 皇宮內的較量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壹章 禦前栽贓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二章 破題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三章 那個女人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四章 夏至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五章 田莊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六章 山裏的月光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七章 對河壹拜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八章 故人相見不相識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零九章 慶余堂裏說來年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章 點卯太常寺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壹章 風起於萍末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二章 關於黑拳的光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三章 大劈棺與小手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四章 送山送水送翠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五章 避暑何須時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六章 湖畔吹來孜然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七章 妖精吵架的典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八章 夏日覓得壹枝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壹十九章 太子駕到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章 升官還是倒黴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壹章 箱子毒針殺殺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二章 北齊來使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三章 談判無藝術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四章 老辣任少卿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五章 東宮之中斟賢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六章 這世上沒有值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七章 那座涼沁沁的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八章 娘娘們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二十九章 穿過妳的黑發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章 匆匆回府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壹章 驚聞北國言君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二章 汙水下的協議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三章 夜宴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四章 千古風流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五章 醉中早有入宮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六章 洪公公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七章 每個人的心中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八章 廣信宮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三十九章 誰是刺客?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章 箱子的秘密(壹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壹章 箱子的秘密(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二章 秋雨後的晴朗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三章 傳單如雪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四章 算術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五章 詩集與言紙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六章 大婚(壹)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七章 大婚(二)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八章 禮物
- [ 免費 ] 第壹百四十九章 思思姑娘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章 蒼山蜜月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壹章 無事之秋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二章 練槍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三章 兩情若是相悅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四章 朝議(壹)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五章 朝議(二)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六章 疑問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七章 回京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八章 二皇子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五十九章 河畔新絲令人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章 狗日的會試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壹章 考官其實是有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二章 春風化雨入春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三章 妳糊我糊大家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四章 驚雷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五章 科場弊案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六章 雨中訪友(壹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七章 雨中訪友(二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八章 閃亮的日子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六十九章 皇榜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章 權臣剛剛上路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壹章 京官的反擊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二章 辯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三章 大鬧刑部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四章 提司!提司!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五章 初登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六章 告訴妳壹個真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七章 人世間的影子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八章 小花
- [ 免費 ] 第壹百七十九章 陰寒的裝備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章 褻瀆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壹章 夜夜夜夜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二章 肖恩出獄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三章 京外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四章 毫無美感的下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五章 馬車春色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六章 白袖招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七章 向肖恩學習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八章 京中殺人細無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八十九章 油傘骨中壹柄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章 白鳥在湖人在心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壹章 司理理的秘密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二章 長公主的願景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三章 出柙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四章 開門,放狗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五章 妳死,我活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六章 草甸驚變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七章 海棠朵朵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八章 以無恥入有德 ...
- [ 免費 ] 第壹百九十九章 無題
- [ 免費 ] 第二百章 海棠春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壹章 心戰前傳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二章 壹字記之曰心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三章 霧渡河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四章 官道邊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五章 上京城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六章 斑駁城墻夜色重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七章 使團入宮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八章 與皇帝聊天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零九章 姓範的牛人很多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章 丫就是壹村姑!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壹章 搖啊搖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二章 使團本是打架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三章 譚武不弄文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四章 秀水街的老鋪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五章 皇商的近況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六章 長寧侯府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七章 您想發財嗎?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八章 關範卿何事?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壹十九章 初見言冰雲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章 撕白袍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壹章 理想主義者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二章 雨夜見沈重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三章 小言脫身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四章 事情不是想像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五章 謀劃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六章 憐子如何不丈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七章 巷中殺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八章 上京暗哨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二十九章 有喜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章 若若要嫁人!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壹章 多多益善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二章 俯瞰越獄事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三章 埋伏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四章 事敗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五章 範閑也尾行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六章 濕柴與黑拳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七章 範閑跳崖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八章 世間遊客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三十九章 永夜之廟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章 逃出神廟的小姑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壹章 今日本章無題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二章 閉目從此閑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三章 怎麽又白了?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四章 何來意閑閑?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五章 走的便是女道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六章 種田喝酒聊天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七章 這世道,這女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八章 關於殿前比武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四十九章 壹俯壹仰壹場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章 皇帝也八卦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壹章 接班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二章 長亭古道丟手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三章 初秋的收割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四章 爭道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五章 家務事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六章 這次第,怎壹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七章 後宅荒唐事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八章 九月裏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五十九章 馬車上的天下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章 出宮做爺去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壹章 獨壹處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二章 處裏來了位年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三章 整風!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四章 新風館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五章 她自重了,妳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六章 戴公公的英明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七章 黑與白的間奏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八章 聖人?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六十九章 宮中奏章驚風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章 安之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壹章 宮前對峙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二章 朝堂激辯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三章 杖責與人品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四章 黑夜裏的明拳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五章 宮裏宮外的青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六章 靖王壽宴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七章 出國留學好不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八章 新繡手帕要不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七十九章 抱月樓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章 桑文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壹章 範壹掌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二章 鬥狠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三章 攔街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四章 擋在馬車前的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五章 子有憂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六章 自古龜公出少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七章 跟我回家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八章 抄樓
- [ 免費 ] 第二百八十九章 兄弟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章 家法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壹章 老範與小範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二章 流放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三章 已經勾引彼同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四章 京都外的夜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五章 收樓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六章 妓女、路人以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七章 京都府外謝必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八章 小恙無妨觀落 ...
- [ 免費 ] 第二百九十九章 藥
- [ 免費 ] 第三百章 墻裏秋千墻外道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壹章 陳園有客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二章 秋林、私語、結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三章 菊花、古劍和酒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四章 菊花、古劍和酒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五章 匕首,又見匕首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六章 傷者在宮中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七章 燭光下的手術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八章 梅園病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零九章 神仙局背後的神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章 大皇子來訪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壹章 封賞與對話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二章 情書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三章 遊園驚夢(上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四章 遊園驚夢(中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五章 遊園驚夢(下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六章 上京城的雪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七章 大宗師,黑布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八章 誰能殺死範提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壹十九章 山居筆記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章 最好的時機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壹章 知母莫若知父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二章 慶國人民關於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三章 猜出花兒來也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四章 布衣宗師的宗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六章 範府的變化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七章 宮中小樓隱風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八章 俱往矣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二十九章 祝您飛黃騰達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章 離前騷(上)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壹章 離前騷(下)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二章 夜泊潁州有賊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三章 慶國最大的壹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四章 有情況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五章 妳們已經被包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六章 我拿什麽供奉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七章 投名狀以及範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八章 壹路銀江收禮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三十九章 樓上樓、人外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章 賣花姑娘與無恥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壹章 恰同學少年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二章 天降祥瑞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三章 端起碗喝粥,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四章 龍擡頭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五章 錢莊與青樓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六章 君子取財之道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七章 順德到了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八章 霸得蠻、耐不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四十九章 內庫罷工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章 欽差大人因何發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壹章 老掌櫃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二章 有自主意識的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三章 有些事情做得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四章 春之道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五章 借妳的手,牽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六章 明家眼中的鵝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七章 扼住命運的咽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八章 洗島
- [ 免費 ] 第三百五十九章 明家母子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章 身在蘇州心在天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壹章 內庫門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二章 乙四房的強盜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三章 大哥,好久不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四章 牽壹發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五章 翹壹指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六章 天女散花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七章 天曉不因鐘鼓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八章 膝下並無黃金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六十九章 月明非為夜行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章 夏明記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壹章 刑房與遺書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二章 家產官司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三章 和諧無比的那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四章 新風館的包子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五章 開樓殺人夜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六章 殺袁驚夢換血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七章 釣魚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八章 明家悲情的背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七十九章 誰的水師?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章 不甘撒手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壹章 宮與朝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二章 殿上挖角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三章 戶部之事(上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四章 戶部之事(下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五章 清查與藝術家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六章 範建的劍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七章 搬起壹團大雪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八章 有理與天威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八十九章 深春之京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章 春和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壹章 景明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二章 波瀾起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三章 誰不驚?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四章 滿城白霜下黑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五章 我於樓上觀民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六章 妳在園外鬧,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七章 蘇州城來了位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八章 妳怎麽敢殺我 ...
- [ 免費 ] 第三百九十九章 壹劍傾人樓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章 華園的頭腦風暴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壹章 那些月兒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二章 被子保佑天下的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三章 棄兒們的聚會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四章 劍與旨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五章 此事不關風月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六章 孩子氣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七章 壹樣的星空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八章 梧州姑爺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零九章 與娘家人的談判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章 老丈人笑談君山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壹章 出山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二章 近城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三章 膠州有人開壽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四章 茅房有人玩暗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五章 再闖府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六章 提督府內壹場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七章 書房宣口諭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八章 迷死人不償命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壹十九章 誰是誰的人?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章 我從遠方趕來赴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壹章 入羊群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二章 略帶腥味的海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三章 大事可為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四章 君臣有心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五章 天子有疾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六章 海風有信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七章 榮歸(壹)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八章 榮歸(二)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二十九章 祖孫、弟妹、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章 慈悲與悶騷是壹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壹章 淡州今日無豆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二章 只論親疏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三章 離開淡州前的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四章 雪夜遇青幡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五章 王十三郎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六章 山谷有雪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七章 白雪紅林黑發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八章 京都別來無恙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三十九章 樞密院前、大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章 何以報?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壹章 種白菜的老爺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二章 誰能敵?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三章 天下有狗,誰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四章 人在廟堂,身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五章 舊輪椅、新輪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六章 三人三思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七章 畫中人、畫外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八章 大哥別說二哥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四十九章 我的人,他們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章 樓外有雪、北方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壹章 洗手做羹湯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二章 心血如壹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三章 禦書房內憶當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四章 抱月樓前笑兄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五章 鴻門宴上道春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六章 鴻門宴上道春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七章 鴻門宴上道春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八章 鴻門宴上道春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五十九章 霧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章 黎明前的雪花、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壹章 大朝會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二章 淡泊公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三章 天下有敵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四章 關卿鳥事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五章 歸宗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六章 君臣之間無曖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七章 記得當時年紀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八章 靴子裏的小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六十九章 宮裏那些……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章 再見長公主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壹章 夜宮裏的寂寞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二章 噢,眼淚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三章 稻草的根在哪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四章 萬物有法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五章 不速則達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六章 破冰如玉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七章 皇族中的另類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八章 生命不能承受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七十九章 我知道妳去年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章 太監也可以改變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壹章 範三寶的由來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二章 為人父母者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三章 第三代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四章 態度決定壹切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五章 招商錢莊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六章 壹個宮女的死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七章 大石壓車誰能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八章 這是壹個陰謀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八十九章 大人物們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章 明園裏的笑聲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壹章 子系中山狼(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二章 子系中山狼(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三章 宮裏的三個夜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四章 半個時辰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五章 皇宮裏的血與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六章 雷雨(上)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七章 雷雨(下) ...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八章 寡人
- [ 免費 ] 第四百九十九章 幽
- [ 免費 ] 第五百章 流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壹章 嘆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二章 坑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三章 新壹代的小怪物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四章 山中的範府小姐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五章 如果妳來投奔我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六章 歸壹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七章 愈沈默愈快樂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八章 清茶、烈酒、草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零九章 荒唐言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章 荒唐事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壹章 君之賤(上)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二章 君之賤(下)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三章 君臨東海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四章 浪花自懸崖上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五章 白雲自高山上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六章 廟中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七章 心中言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八章 月兒彎彎照東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壹十九章 長弓封夜山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章 遮月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壹章 投奔怒海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二章 海船上的那顆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三章 追捕(上)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四章 追捕(中)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五章 追捕(下)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六章 驚艷壹槍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七章 傷心小箭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八章 大宗師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二十九章 人世間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章 會東山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壹章 大行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二章 京都的蟬鳴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三章 每個人的心上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四章 秋意初起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五章 請借先生骨頭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六章 悲聲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七章 他其實壹直都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八章 羊蔥巷中的密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三十九章 誰能長有淡泊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章 有子逾墻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壹章 誰家府上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二章 殺人從來不亮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三章 第壹次拔出靴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四章 那壹夜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五章 閑推月下門及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六章 強悍,因為決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七章 皇城內外盡殺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八章 數枝箭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四十九章 多情太監無情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章 狠手(上)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壹章 狠手(下)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二章 逃難中的陳萍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三章 請君入甕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四章 正陽門前的伏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五章 光榮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六章 奪旗、奪勢、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七章 城頭祭出神主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八章 箕坐於城不得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五十九章 誰將君心擬火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章 且以黑騎開序幕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壹章 荊戈刺秦!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二章 殺秦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三章 壹眼瞬間之無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四章 定州軍的定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五章 太平別院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六章 花壹樹、琴千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七章 雲無心以出袖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八章 王道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六十九章 如瀑入海,如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章 大東山上的因果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壹章 紙入湖而魚動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二章 青花辭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三章 有尊嚴的生存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四章 老姜漸漸淡去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五章 憤怒的葡萄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六章 麥田裏的守望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七章 父與子的下半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八章 聆鐘
- [ 免費 ] 第五百七十九章 百年孤獨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章 妳是我的小棉襖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壹章 入樓出樓漸溫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二章 皇帝的心意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三章 送戰友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四章 青山遮不住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五章 我們的不滿的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六章 流年裏的官司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七章 定州內的胡歌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八章 大將軍府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八十九章 烈酒暖心腸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章 斷刀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壹章 邊城故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二章 王帳走出來的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三章 單於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四章 兩年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五章 湖畔的海棠花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六章 三天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七章 心戰後傳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八章 秋原、朝陽、 ...
- [ 免費 ] 第五百九十九章 歸來
- [ 免費 ] 第六百章 窗外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壹章 把那風景都看透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二章 在城門上目光註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三章 城門舊事非故人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四章 王家小姐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五章 收不收,這不是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六章 算盤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七章 天子之雷及範閑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八章 壹樣的月光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零九章 醫者何心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章 夜半歌聲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壹章 兩院間的渠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二章 東風吹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三章 戲至冬日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四章 春來我去也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五章 同壹條路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六章 周公為師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七章 閑來斬梅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八章 影隨我身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壹十九章 人生何處不重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章 山居中的女子與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壹章 斷楊入廬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二章 廬中客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三章 暮色中的秘密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四章 真正的殿前歡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五章 壹朝天子壹朝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六章 梳頭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七章 劍廬裏的坑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八章 老家夥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二十九章 好大壹棵樹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章 壹眼瞬間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壹章 三人行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二章 拔劍四顧心茫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三章 非聖人不能用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四章 種毒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五章 我們都是顏色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六章 浪花退去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七章 回京求官去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八章 議親議功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三十九章 搶院奪權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章 壹夜長大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壹章 別院之間苦心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二章 墳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三章 分手擂臺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四章 壹杯淡茶知冷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五章 席中假孟浪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六章 太學裏的黑傘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七章 春園亂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八章 口子
- [ 免費 ] 第六百四十九章 犯錯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章 魚腸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壹章 農夫、山莊、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二章 十家村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三章 天之公道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四章 灑落人間的星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五章 意誌,即是王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六章 廟,螞蟻,冊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七章 滿身風雨,我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八章 滿身風雨,我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五十九章 滿身風雨,我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章 空有壹物,劍有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壹章 天下銀根,必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二章 開廬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三章 應作如是想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四章 簡單的征服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五章 平亂之心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六章 歸路有血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七章 風起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八章 娘子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六十九章 都是京都來的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章 拼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壹章 天生壹對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二章 朕要那條老狗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三章 君子、夥伴、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四章 夜風中的輪椅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五章 兩個人的戰爭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六章 壹輛車的孤單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七章 數十年的往事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八章 那又如何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七十九章 監天察地不肯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章 陳萍萍的復仇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壹章 禦書房內竹開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二章 壹根手指與監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三章 京都亂,紅燭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四章 笑看英雄不等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五章 笑看英雄不等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六章 笑看英雄不等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七章 雨中送陳萍萍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八章 又無題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八十九章 長睡範府不願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章 夢中雪山,盆中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壹章 洗手除官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二章 七日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三章 啟年小組踏上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四章 慶廟有雨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五章 廟的名,人的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六章 準備著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七章 宮中的範家小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八章 君臣相見可能 ...
- [ 免費 ] 第六百九十九章 是,陛下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章 獻芹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壹章 看,上去很美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二章 京都閑人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三章 北方有變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四章 雪花背後的真相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五章 冬又至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六章 壹敗之西胡悲歌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七章 定西涼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八章 亂江南
- [ 免費 ] 第七百零九章 京華江南皆有血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章 誰在京都殺四方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壹章 殿前歡盡須斷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二章 布衣單劍朝天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三章 布衣單劍朝天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四章 布衣單劍朝天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五章 布衣單劍朝天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六章 布衣單劍朝天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七章 蒼山有雪劍有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八章 蒼山有雪劍有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壹十九章 蒼山有雪劍有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章 蒼山有雪劍有霜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壹章 假山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二章 人心向北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三章 人在旅途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四章 寒雪勿亂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五章 壹夜北風緊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六章 從前有座山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七章 山裏有座廟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八章 廟裏有個人(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二十九章 廟裏有個人(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章 廟裏有個人(下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壹章 那個人講了壹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二章 輻射風情畫以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三章 壹個人的孤單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四章 最強,人的名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五章 田園將蕪胡不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六章 田園將蕪胡不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七章 暮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八章 枯
- [ 免費 ] 第七百三十九章 午(上)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章 午(下)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壹章 玻璃花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二章 皇城前,下雨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三章 宮前行走誰折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四章 南慶十二年的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五章 南慶十二年的 ...
- [ 免費 ] 第七百四十六章 南慶十二年的 ...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四百五十八章 鴻門宴上道春秋(終)
2018-7-4 10:04
這世道,無官不貪,只看貪大貪小罷了,滿朝盡是蛀蟲,只看蟲身是肥是瘦,不如此,慶國的朝廷上為何會硬生生突起壹個叫做監察院的畸形院司?
但正如範閑在壹處裏整風時發現的那樣,監察院也是人組成的,有人的地方,就有官場,監察院想壹世這樣冷厲下去,基本上不可能。
而且監察院不是神仙,三品以上的,它管不著,皇帝不賜旨,軍方的事情它也管不著。就算陳萍萍和範閑加起來,監察院也不可能改變太多的現狀,歸根結底壹句話,監察院不是查貪官,只是依著皇帝的意思時不時清壹清吏治,平息壹下民怨,騰出壹些空子,維持壹下統治。
若真要查去,陳萍萍園子裏的美人兒,範閑在內庫裏撈的油水,得往外吐多久……遑論那位坐在皇宮裏的九五至尊。
別說皇帝不用貪,他是天下至貪,貪了整個天下,監察院能怎嘀?
……
……
但正因為人人皆貪,所以當監察院因為範閑的癲狂而要做些什麽的時候,是顯得那樣的水到渠成,相當自然。在這個黑夜裏,監察院壹處全員出動,向著那些巷中街角的府邸撲去,不知道逮了多少與二皇子、信陽方面聯系緊密的下層官員。
三品以上自然是壹個不能動,可是這些下層官員才是朝廷真正需要憑恃的幹臣。今夜抱月樓中諸人已然知曉了監察院先前的行動,又得到了範閑的親口承認,不由面上露出無比震驚的表情。
樞密院副使曲向東沈默了下來,深深地看了範閑壹眼,沒有再說什麽。今夜的消息雖不明確,但看得出來,監察院首沖的目標還是信陽和二皇子壹系,與軍方沒有太深的牽連。
他雖然不明白範閑為什麽會忽然間使出這種等而下之的手段,但是監察院的行動力與範閑的狠厲,已經讓他感到了壹絲畏懼。
樓中美人在懷,樓外殺人捕人,便有那雪,又豈能將血腥味道全數掩住。
不是所有的人都因為這突如其來的消息陷入了沈默,當那五名報信的官員小心翼翼退出屏風之後,大皇子沈著臉,望著範閑問道:“為什麽?”
監察院與信陽壹系的沖突由來已久,發端於六年前的內庫之爭,埋因於二皇子借宴請欲在牛欄街上刺殺範閑壹事,又有眾人所坐的抱月樓引出的那個秋天的故事。
在那個秋天裏,範閑奪了抱月樓,殺了謝必安,陰了京都府,毀了二皇子與靖王世子李弘成的名聲,生生將北方的崔家打成了叛逆。
秋天之後的這壹年,範閑下江南,鎮明家,收內庫,於膠州殺常昆。
在所有人看來,範閑對二皇子和信陽壹系的報復已經足夠嚴厲,撈回了足夠多的好處,沒道理在今天的夜裏如此強橫地再次出手。
範閑沈默了少許後,平靜說道:“為什麽?因為本官奉旨清查吏治。”
席間壹片沈默,太子高坐於上沒有去看範閑,反而帶著幾絲頗堪捉摸的神色,看著二皇子的面色。大皇子搖頭嘆息道:“京中太平沒兩天,妳們怎麽就不能消停壹些?”
範閑知道大皇子說的是真心話,這位如今的禁軍大統領自幼與二皇子交好,但因為寧才人和婉兒的緣故,現如今卻是站在自己這壹方,身處其中,自然難免有些難為。他聽著這話,忍不住嘆息道:“太平?我壹年沒有回京,看來京都就太平了壹整年。莫非我真是個災星……難怪在京都郊外的山谷裏,沒有人肯讓我太平些。”
席間再次沈默,諸位大人物隱約明白,這是範閑在為山谷之事找場面,只是……這場面找的有些太大,太荒唐了。
“世上很多事情都很荒唐。”範閑似乎知道這些大人物的心裏在想些什麽,自嘲說道:“就像山谷裏下官被刺殺壹事,朝廷壹直在查著,可是就因為沒有證據,便始終拿不出個說法來。”
他緩緩說道:“誰來理會我的屬下?先前講過,我那名車夫在第壹枝弩箭到來之時,我想將他搶回廂中,他卻硬生生站了起來,替我擋了壹擋……我時常在問自己,如果壹直尋不出什麽證據,我便壹日不能為他做些什麽?”
江南總督薛清意味深長地看了範閑壹眼。
太子緩緩說道:“朝廷自然是要查的。”這是他今夜第三次說這句話了。
範閑點點頭,笑道:“便是這件事情,讓我忽然想到了壹個很久以前聽過的故事。”
……
……
“從前的森林裏,有壹只小白兔,它壹大早就高高興興地出了門,然後它遇見了大灰狼,大灰狼壹把抓住小白兔‘啪啪!’抽了它兩個大嘴巴,然後說:我叫妳不戴帽子!”
眾人面面相覷,不知道為什麽範閑忽然會講起這種小孩子聽的故事來,只聽著範閑繼續說:“第二天,小白兔戴上帽子又出門了,走著走著又遇見了大灰狼,大灰狼又壹把抓過小白兔——‘啪啪!’抽了它兩個大嘴巴:我讓妳戴帽子!”
“小白兔非常郁悶,就跑到老虎那裏去告大灰狼的狀,老虎聽了小白兔的苦訴,痛心說道,妳放心好了,我自然會替妳主持公道……接著,老虎找來了大灰狼對他說:老狼,今天上午小白兔來投訴妳,說妳沒事找事老是欺負它,妳看妳能不能換個理由揍它,比如妳可以說:兔子,妳去給我找塊肉來……”
“要是它找來肥的妳就說妳要瘦的,要是它找來瘦的妳就說妳要肥的,這樣妳不就又可以揍它了嗎?要不妳就讓它幫妳找母兔子,它要找了豐滿的妳就說妳喜歡苗條的,它要找了苗條的妳就說妳喜歡豐滿的!”
範閑講故事講的很認真,但用辭卻極為幼稚荒唐,不過席間的眾人卻露出了深思的表情,包括太子與薛清在內都若有所思,隱約聽明白了,那老虎指的是誰……卻沒有人敢宣諸表情。
範閑喝了壹口酒,認真說道:“老狼聽了以後十分高興,連誇老虎聰明。可是他們的對話卻被在房子外面鋤草的小白兔聽見了……”
“很巧?不過故事就是無巧不成書。接著說……”範閑冷笑著說道:“第三天,小白兔又出門了,又在半路上遇見大灰狼,大灰狼說:兔子,妳去給我找塊肉來!”
“小白兔說:妳要肥的還是瘦的。”
“大灰狼皺了皺眉頭,笑了笑心想,還好還有第二招:算了算了,不要肉了,妳去給我找個母兔子來。”
“小白兔說:妳喜歡豐滿的,還是喜歡苗條的?”
……
……
範閑皺緊了眉頭,搖頭說道:“碰見這麽壹個狡猾的兔子,妳說這可怎麽辦?”
席間諸人也開始想,大灰狼接下來會做什麽?不由有些好奇範閑接下來會怎麽講。範閑抿了抿微幹的雙唇,笑著說道:
“大灰狼楞了壹下,‘啪啪’抽了小白兔兩個大嘴巴,罵道……我叫妳不戴帽子!”
……
……
我叫妳不戴帽子!
世間最無理、無恥、無聊、無稽的壹個理由,便是最充分的理由,也等於說是不需要理由,看的就是誰拳頭大壹些。
範閑最後認真說道:“我不想繼續當小白兔,我要當大灰狼。”
這是他前世聽的壹個笑話,只是今夜講起來卻有些沈重。席間諸人本應是哈哈大笑,此時卻沒有人笑的出來。
眾人心中喟嘆,山谷狙殺範閑壹事,只怕永世也查不清楚,而今夜監察院暗殺八家將,在全無證據,範閑不承認的情況下,也會永世查不清楚。世上的事情本來就是這樣,既然先天敵對的彼此都找不到充分的理由,那何必還找理由?權力場便有若山野,狼逐兔奔,虎視於旁,自然之理。
※※※
酒宴至此,雖未殘破,這些大人物們卻早已無心繼續。京都的官場,本來就已無法平靜,今夜更是鬧的難堪,雖則監察院是借夜行事,想必不會驚動太多京都百姓,可是這些大人物們依然要趕著回府回衙,去處理壹應善後事宜,同時為迎接新的局面做出心理上以及官面上的準備。
範閑送薛清到了門口,薛清臨去之時,回頭溫和壹笑,說道:“狼是壹種群居動物,妳不要把自己搞成了壹匹孤狼,那樣總是危險的。”
範閑心頭微溫,壹揖謝過。
薛清沈默片刻後又道:“聖上雖然點過頭,但還是要註意壹下分寸。尤其是朝廷的臉面,總要保存壹些。”
範閑再次應下。
待幾位大人物的車轎緩緩離開抱月樓,太子殿下也伸著懶腰,抱著美人兒走了下來,早有身旁服侍的人將那名貴的華裘披到了他的身上。太子看了範閑壹眼,笑道:“今夜這出戲倒是好看。”
太子將身旁的女人與四周的閑人驅開,望著範閑平靜說道:“話說壹年前那個秋天,本宮看妳與二哥演的那上半出戲時,也覺著好看……細細思量壹番,倒是本宮與妳,並未如何。”
範閑微微壹凜,這位表現與往常大異的太子殿下這番話不知道是什麽意思。
“本宮與妳之間,從來沒有任何問題。”太子微閉雙眼,緩緩說道:“如果有問題,那是當年的問題,不應該成為妳我之間的問題,希望妳記住這壹點。”
範閑明白,他與太子之間,其實壹直保持著某種和平,只是橫亙著皇後當年參與的那件事情,則成為了天生的敵人。他不明白太子這麽說,是準備做些什麽,但是範閑相信,太子總不可能為了爭取自己的支持,會眼看著自己去殺了他的老母。
所以……只是說說罷了。
※※※
屏風內並未人去座空,二皇子很奇怪地留了下來,他看著從樓下走上來的範閑,微微壹笑,將自己的左手緩緩放到案面之上,努力抑制著自己內心深處的那些荒謬感覺,用兩只手指拈了個南方貢來的青果緩緩嚼著。
範閑坐在了他的對面,端起酒壺,開始自斟自飲,倏然盡十杯。
大皇子抱著酒甕,於壹旁痛飲,似乎想謀壹醉。
範閑放下酒杯,拍拍手掌,三皇子規規矩矩地從簾後走了出來,有些為難地看了大哥和二哥壹眼,然後坐到了自己老師的身邊。
大皇子不贊同地看了範閑壹眼,眼神裏似乎在說,大人的事情,何必把小的也牽扯進來。
此時抱月樓三樓花廳,便是三位皇子,加上範閑壹個,如果不算先前離開的太子,慶國皇帝在這個世上留的血脈,算是到齊了。
先前的鴻門宴,已然變成了氣氛古怪的家宴。
“妳害怕了。”
二皇子放下啃了壹半的青果,盯著範閑的雙眼,柔聲說道。
範閑端酒杯的手僵了僵,緩緩應道:“我怕什麽?”
“妳不怕,今夜何必做這麽大的動作?”二皇子微微壹笑,輕柔說道:“只有內心畏懼的人,才會像妳今夜這樣胡亂出手,妳殺我家將,捕我心腹,難道對這大局有任何影響?”
範閑深深吸了壹口氣,面色平靜了下來,說道:“此間無外人,直說亦無妨,妳的手下,今天被我清幹凈了,但是……妳沒有證據,就如同先前說過的那般,山谷狙殺的事情,我也沒有證據,可是妳們依然做了。”
“山谷狙殺的事情,我不知情,我未參與。”二皇子盯著範閑的眼睛,很認真地說道。
範閑搖搖頭:“那牛欄街的事情呢?小白兔被扇了太多次耳光……我承認,山谷的事情我至今不知道是誰做的,但這並不妨礙我出手。”
他低頭說道:“四面八方都是敵人,既然不知道是哪個敵人做的,我當然要放亂箭,如果偶爾射中正主兒,那是我得了便宜,射中旁的人,我也不吃虧,也是占便宜。”
“牛欄街……”二皇子薄唇的笑容裏閃過壹絲苦澀,“幾年前的事情,想來,也就這麽壹件事情,妳卻壹直記到了今天。”
範閑擡起頭來,平靜說道:“我是壹個很記仇的人,而妳也清楚,這件事情,和記仇並沒有太大關系,妳壹日不罷手,我便會壹日不歇地做下去。”
沒有大臣在場,沒有太子在場,範閑與二皇子這壹對氣質極為相近的年輕權貴,說的話,也顯得是如此的直接、幹脆,都是心思纖細的人,知道彼此間不需要用太多的言語遮掩。
二皇子深深看了範閑身邊的三皇子壹眼,忽然開口說道:“有時候,本王會覺得人生不公平……不說崔家明家那些事情,只說這宮中,我疼愛的妹妹嫁給妳做了妻子,我自幼友善的兩位兄弟,如今卻都站在妳這壹邊。”
二皇子擡起頭來,那張俊秀的面容裏夾著壹絲隱怒:“如果是本王能力不如妳倒也罷了,可是……這只不過是因為壹些很荒唐的理由,壹些前世的故事,而造成了如今的局面。如果父皇肯將監察院交給我,難道本王會做的比妳差?如果父皇肯將內庫交給我,難道本王就真沒有能力將國庫變得充裕起來?修大堤,妳我都不會修,妳我都只能出銀子……安之啊安之,妳不覺得很不公平嗎?畢竟我才是正牌的皇子。”
範閑沈默了許久,心知自己在慶國這光怪陸離的壹生,如今所能獲得的這種畸形權勢……全然是因為當年那個女人的遺澤,當然,那個女人也為自己帶來了無數的麻煩與兇險。二皇子所言,其實並非全無道理,若自己與他易地而處,自己不見得比他做的更好,二皇子不是沒有能力,而是壹直沒有施展能力的舞臺。
他緩緩說道:“世事從無如果二字。”
“不錯,所以妳如今左手監察院,右手內庫……”二皇子微微譏諷說道:“如此大的權勢,想來也只有當年令堂曾經擁有過……所以,妳現在提前開始怕了。”
範閑的面容再次僵了壹下。
二皇子平靜說道:“妳想過將來沒有?妳今日究竟是為誰辛苦為誰忙?”他眼光微轉,看了三皇子壹眼,笑道:“我皇室子弟,沒壹個是好相與的,妳自己也是其中壹屬,當然明白其中道理。”
三皇子低著頭,根本不敢插話。範閑知道老二並不是在危言聳聽,只是他有自己的打算與計劃。
二皇子淡淡說道:“妳是真的怕了……想壹想妳現在這孤臣快要往絕臣的路上走,日後不論是誰登基,這慶國怎麽容得下妳?怎麽容得下監察院?”
範閑平靜聽著。二皇子繼續說道:“妳之所以怕,是因為妳是聰明人,妳知道妳如今權勢雖然滔天,卻只是浮雲而已,甚至及不上壹張薄紙結實。”
二皇子嘆息著:“因為妳手頭的壹切權力,都是父皇給妳的,只需要壹道詔書,妳就可以被貶下凡塵,永世不得翻身……父皇雖然寵愛妳,但也不是沒有提防妳,這幾年任何路子都由著妳在闖,卻絕對不會讓妳染指軍隊,其中深意,想來不用我提醒。”
最後二皇子總結道:“正因為妳怕了,所以妳要……自削權柄!”
……
……
大皇子喝了壹口酒,冷漠地看著自己的兩個兄弟像兩只鬥雞壹樣說著話。
範閑沈默了很久,沒有接二皇子這句話,只是輕聲說道:“權力本是浮雲。這天下何曾有過不敗的將軍,不滅的大族?殿下是皇子,心在天下,我卻只是臣子,我要保我自身及家族康寧……”
二皇子截住他的話頭,冷冷說道:“本王知道,妳堂堂詩仙,向來不以皇室血脈為榮,反而刻意回避此點。但妳捫心自問,若不是妳厭惡的皇室血脈,妳豈能活到今日還能活的如此榮光?”
壹座四兄弟,二人沈默,二人對峙。
“放手吧。”二皇子誠懇說道:“妳的力量其實都是虛的。妳不敢殺本王,便只能眼看著壹天壹天地過去,而妳卻壹天壹天地危險。既然妳已經察覺到了這點,為什麽不幹脆放手的更徹底壹些?以妳在這天下的聲名,妳是婉兒的相公,妳是父皇的兒子,妳是北齊的座上客……誰會為難妳?誰敢冒著不必要的風險為難妳?靈兒說過,妳最喜歡周遊世界,那何必還困於這險惡京都,無法自拔?”
範閑的眉頭漸漸地皺了起來,手指頭緩緩捏弄著酒杯,開口說道:“殿下,先前便說過……我與妳的想法是壹樣的。”
他擡起頭來,面上容光壹湛,望著二皇子平靜說道:“壹年前在這樓子外的茶鋪裏就曾經說過,妳不放手,我便要打到妳放手,而且事實證明了,如今的我,有這個實力……茶鋪裏的八家將,妳再也看不到了,這就是很充分的證明。”
聽到茶鋪二字,二皇子面容頓時壹凝,想到了壹年多前的秋天,在抱月樓外茶鋪裏與範閑的那番對話。其時的對話,是發生在王爺與臣子之間,而壹年過去,範閑的權勢像吹氣球壹樣地膨脹起來,最關鍵的是,兩個人的真實身份也逐漸平齊了。
“我為何放手?”二皇子有些神經質地自嘲說道。
“殿下中了長公主的毒,我來替妳解。”範閑壹句不退,冷漠說道:“當初的話依然有效,殿下何時與長公主保持距離,真正放手,本官許妳……壹世平安。”
“妳憑什麽?”二皇子認真地看著範閑的眼睛,“難道就憑監察院和銀子?”
範閑搖搖頭,說道:“不憑什麽,只是我欠皇妃壹個人情,欠婉兒壹個承諾,今夜之事,殿下應該心中清楚,我便是要清空殿下私己的力量,將妳從這潭爛水裏打將出來。”
二皇子壹想到今夜自己所遭受的巨大損失,終於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那抹淒寒,陰怒說道:“為什麽是我?父皇不止我壹個兒子,妳也是!”
“我沒有壹絲野望,我只是壹位臣子。”範閑說道:“再過兩天,殿下便會知道我的誠意。至於其余的殿下,壹位是我的學生,我會把他打乖壹些,大殿下更喜歡喝酒,太子我不理會,只好針對您了……您說的對,這血脈總是值得尊重壹二的,所以我會盡壹切力量阻止那種可怕的事情發生。”
二皇子心頭壹寒。屏風有壹個縫隙沒有擋好,冬日裏的寒風開始在抱月樓內部緩緩飄蕩。範閑最後說道:“請殿下牢記壹點,陛下春秋正盛,不希望看見這種事情發生。”
但正如範閑在壹處裏整風時發現的那樣,監察院也是人組成的,有人的地方,就有官場,監察院想壹世這樣冷厲下去,基本上不可能。
而且監察院不是神仙,三品以上的,它管不著,皇帝不賜旨,軍方的事情它也管不著。就算陳萍萍和範閑加起來,監察院也不可能改變太多的現狀,歸根結底壹句話,監察院不是查貪官,只是依著皇帝的意思時不時清壹清吏治,平息壹下民怨,騰出壹些空子,維持壹下統治。
若真要查去,陳萍萍園子裏的美人兒,範閑在內庫裏撈的油水,得往外吐多久……遑論那位坐在皇宮裏的九五至尊。
別說皇帝不用貪,他是天下至貪,貪了整個天下,監察院能怎嘀?
……
……
但正因為人人皆貪,所以當監察院因為範閑的癲狂而要做些什麽的時候,是顯得那樣的水到渠成,相當自然。在這個黑夜裏,監察院壹處全員出動,向著那些巷中街角的府邸撲去,不知道逮了多少與二皇子、信陽方面聯系緊密的下層官員。
三品以上自然是壹個不能動,可是這些下層官員才是朝廷真正需要憑恃的幹臣。今夜抱月樓中諸人已然知曉了監察院先前的行動,又得到了範閑的親口承認,不由面上露出無比震驚的表情。
樞密院副使曲向東沈默了下來,深深地看了範閑壹眼,沒有再說什麽。今夜的消息雖不明確,但看得出來,監察院首沖的目標還是信陽和二皇子壹系,與軍方沒有太深的牽連。
他雖然不明白範閑為什麽會忽然間使出這種等而下之的手段,但是監察院的行動力與範閑的狠厲,已經讓他感到了壹絲畏懼。
樓中美人在懷,樓外殺人捕人,便有那雪,又豈能將血腥味道全數掩住。
不是所有的人都因為這突如其來的消息陷入了沈默,當那五名報信的官員小心翼翼退出屏風之後,大皇子沈著臉,望著範閑問道:“為什麽?”
監察院與信陽壹系的沖突由來已久,發端於六年前的內庫之爭,埋因於二皇子借宴請欲在牛欄街上刺殺範閑壹事,又有眾人所坐的抱月樓引出的那個秋天的故事。
在那個秋天裏,範閑奪了抱月樓,殺了謝必安,陰了京都府,毀了二皇子與靖王世子李弘成的名聲,生生將北方的崔家打成了叛逆。
秋天之後的這壹年,範閑下江南,鎮明家,收內庫,於膠州殺常昆。
在所有人看來,範閑對二皇子和信陽壹系的報復已經足夠嚴厲,撈回了足夠多的好處,沒道理在今天的夜裏如此強橫地再次出手。
範閑沈默了少許後,平靜說道:“為什麽?因為本官奉旨清查吏治。”
席間壹片沈默,太子高坐於上沒有去看範閑,反而帶著幾絲頗堪捉摸的神色,看著二皇子的面色。大皇子搖頭嘆息道:“京中太平沒兩天,妳們怎麽就不能消停壹些?”
範閑知道大皇子說的是真心話,這位如今的禁軍大統領自幼與二皇子交好,但因為寧才人和婉兒的緣故,現如今卻是站在自己這壹方,身處其中,自然難免有些難為。他聽著這話,忍不住嘆息道:“太平?我壹年沒有回京,看來京都就太平了壹整年。莫非我真是個災星……難怪在京都郊外的山谷裏,沒有人肯讓我太平些。”
席間再次沈默,諸位大人物隱約明白,這是範閑在為山谷之事找場面,只是……這場面找的有些太大,太荒唐了。
“世上很多事情都很荒唐。”範閑似乎知道這些大人物的心裏在想些什麽,自嘲說道:“就像山谷裏下官被刺殺壹事,朝廷壹直在查著,可是就因為沒有證據,便始終拿不出個說法來。”
他緩緩說道:“誰來理會我的屬下?先前講過,我那名車夫在第壹枝弩箭到來之時,我想將他搶回廂中,他卻硬生生站了起來,替我擋了壹擋……我時常在問自己,如果壹直尋不出什麽證據,我便壹日不能為他做些什麽?”
江南總督薛清意味深長地看了範閑壹眼。
太子緩緩說道:“朝廷自然是要查的。”這是他今夜第三次說這句話了。
範閑點點頭,笑道:“便是這件事情,讓我忽然想到了壹個很久以前聽過的故事。”
……
……
“從前的森林裏,有壹只小白兔,它壹大早就高高興興地出了門,然後它遇見了大灰狼,大灰狼壹把抓住小白兔‘啪啪!’抽了它兩個大嘴巴,然後說:我叫妳不戴帽子!”
眾人面面相覷,不知道為什麽範閑忽然會講起這種小孩子聽的故事來,只聽著範閑繼續說:“第二天,小白兔戴上帽子又出門了,走著走著又遇見了大灰狼,大灰狼又壹把抓過小白兔——‘啪啪!’抽了它兩個大嘴巴:我讓妳戴帽子!”
“小白兔非常郁悶,就跑到老虎那裏去告大灰狼的狀,老虎聽了小白兔的苦訴,痛心說道,妳放心好了,我自然會替妳主持公道……接著,老虎找來了大灰狼對他說:老狼,今天上午小白兔來投訴妳,說妳沒事找事老是欺負它,妳看妳能不能換個理由揍它,比如妳可以說:兔子,妳去給我找塊肉來……”
“要是它找來肥的妳就說妳要瘦的,要是它找來瘦的妳就說妳要肥的,這樣妳不就又可以揍它了嗎?要不妳就讓它幫妳找母兔子,它要找了豐滿的妳就說妳喜歡苗條的,它要找了苗條的妳就說妳喜歡豐滿的!”
範閑講故事講的很認真,但用辭卻極為幼稚荒唐,不過席間的眾人卻露出了深思的表情,包括太子與薛清在內都若有所思,隱約聽明白了,那老虎指的是誰……卻沒有人敢宣諸表情。
範閑喝了壹口酒,認真說道:“老狼聽了以後十分高興,連誇老虎聰明。可是他們的對話卻被在房子外面鋤草的小白兔聽見了……”
“很巧?不過故事就是無巧不成書。接著說……”範閑冷笑著說道:“第三天,小白兔又出門了,又在半路上遇見大灰狼,大灰狼說:兔子,妳去給我找塊肉來!”
“小白兔說:妳要肥的還是瘦的。”
“大灰狼皺了皺眉頭,笑了笑心想,還好還有第二招:算了算了,不要肉了,妳去給我找個母兔子來。”
“小白兔說:妳喜歡豐滿的,還是喜歡苗條的?”
……
……
範閑皺緊了眉頭,搖頭說道:“碰見這麽壹個狡猾的兔子,妳說這可怎麽辦?”
席間諸人也開始想,大灰狼接下來會做什麽?不由有些好奇範閑接下來會怎麽講。範閑抿了抿微幹的雙唇,笑著說道:
“大灰狼楞了壹下,‘啪啪’抽了小白兔兩個大嘴巴,罵道……我叫妳不戴帽子!”
……
……
我叫妳不戴帽子!
世間最無理、無恥、無聊、無稽的壹個理由,便是最充分的理由,也等於說是不需要理由,看的就是誰拳頭大壹些。
範閑最後認真說道:“我不想繼續當小白兔,我要當大灰狼。”
這是他前世聽的壹個笑話,只是今夜講起來卻有些沈重。席間諸人本應是哈哈大笑,此時卻沒有人笑的出來。
眾人心中喟嘆,山谷狙殺範閑壹事,只怕永世也查不清楚,而今夜監察院暗殺八家將,在全無證據,範閑不承認的情況下,也會永世查不清楚。世上的事情本來就是這樣,既然先天敵對的彼此都找不到充分的理由,那何必還找理由?權力場便有若山野,狼逐兔奔,虎視於旁,自然之理。
※※※
酒宴至此,雖未殘破,這些大人物們卻早已無心繼續。京都的官場,本來就已無法平靜,今夜更是鬧的難堪,雖則監察院是借夜行事,想必不會驚動太多京都百姓,可是這些大人物們依然要趕著回府回衙,去處理壹應善後事宜,同時為迎接新的局面做出心理上以及官面上的準備。
範閑送薛清到了門口,薛清臨去之時,回頭溫和壹笑,說道:“狼是壹種群居動物,妳不要把自己搞成了壹匹孤狼,那樣總是危險的。”
範閑心頭微溫,壹揖謝過。
薛清沈默片刻後又道:“聖上雖然點過頭,但還是要註意壹下分寸。尤其是朝廷的臉面,總要保存壹些。”
範閑再次應下。
待幾位大人物的車轎緩緩離開抱月樓,太子殿下也伸著懶腰,抱著美人兒走了下來,早有身旁服侍的人將那名貴的華裘披到了他的身上。太子看了範閑壹眼,笑道:“今夜這出戲倒是好看。”
太子將身旁的女人與四周的閑人驅開,望著範閑平靜說道:“話說壹年前那個秋天,本宮看妳與二哥演的那上半出戲時,也覺著好看……細細思量壹番,倒是本宮與妳,並未如何。”
範閑微微壹凜,這位表現與往常大異的太子殿下這番話不知道是什麽意思。
“本宮與妳之間,從來沒有任何問題。”太子微閉雙眼,緩緩說道:“如果有問題,那是當年的問題,不應該成為妳我之間的問題,希望妳記住這壹點。”
範閑明白,他與太子之間,其實壹直保持著某種和平,只是橫亙著皇後當年參與的那件事情,則成為了天生的敵人。他不明白太子這麽說,是準備做些什麽,但是範閑相信,太子總不可能為了爭取自己的支持,會眼看著自己去殺了他的老母。
所以……只是說說罷了。
※※※
屏風內並未人去座空,二皇子很奇怪地留了下來,他看著從樓下走上來的範閑,微微壹笑,將自己的左手緩緩放到案面之上,努力抑制著自己內心深處的那些荒謬感覺,用兩只手指拈了個南方貢來的青果緩緩嚼著。
範閑坐在了他的對面,端起酒壺,開始自斟自飲,倏然盡十杯。
大皇子抱著酒甕,於壹旁痛飲,似乎想謀壹醉。
範閑放下酒杯,拍拍手掌,三皇子規規矩矩地從簾後走了出來,有些為難地看了大哥和二哥壹眼,然後坐到了自己老師的身邊。
大皇子不贊同地看了範閑壹眼,眼神裏似乎在說,大人的事情,何必把小的也牽扯進來。
此時抱月樓三樓花廳,便是三位皇子,加上範閑壹個,如果不算先前離開的太子,慶國皇帝在這個世上留的血脈,算是到齊了。
先前的鴻門宴,已然變成了氣氛古怪的家宴。
“妳害怕了。”
二皇子放下啃了壹半的青果,盯著範閑的雙眼,柔聲說道。
範閑端酒杯的手僵了僵,緩緩應道:“我怕什麽?”
“妳不怕,今夜何必做這麽大的動作?”二皇子微微壹笑,輕柔說道:“只有內心畏懼的人,才會像妳今夜這樣胡亂出手,妳殺我家將,捕我心腹,難道對這大局有任何影響?”
範閑深深吸了壹口氣,面色平靜了下來,說道:“此間無外人,直說亦無妨,妳的手下,今天被我清幹凈了,但是……妳沒有證據,就如同先前說過的那般,山谷狙殺的事情,我也沒有證據,可是妳們依然做了。”
“山谷狙殺的事情,我不知情,我未參與。”二皇子盯著範閑的眼睛,很認真地說道。
範閑搖搖頭:“那牛欄街的事情呢?小白兔被扇了太多次耳光……我承認,山谷的事情我至今不知道是誰做的,但這並不妨礙我出手。”
他低頭說道:“四面八方都是敵人,既然不知道是哪個敵人做的,我當然要放亂箭,如果偶爾射中正主兒,那是我得了便宜,射中旁的人,我也不吃虧,也是占便宜。”
“牛欄街……”二皇子薄唇的笑容裏閃過壹絲苦澀,“幾年前的事情,想來,也就這麽壹件事情,妳卻壹直記到了今天。”
範閑擡起頭來,平靜說道:“我是壹個很記仇的人,而妳也清楚,這件事情,和記仇並沒有太大關系,妳壹日不罷手,我便會壹日不歇地做下去。”
沒有大臣在場,沒有太子在場,範閑與二皇子這壹對氣質極為相近的年輕權貴,說的話,也顯得是如此的直接、幹脆,都是心思纖細的人,知道彼此間不需要用太多的言語遮掩。
二皇子深深看了範閑身邊的三皇子壹眼,忽然開口說道:“有時候,本王會覺得人生不公平……不說崔家明家那些事情,只說這宮中,我疼愛的妹妹嫁給妳做了妻子,我自幼友善的兩位兄弟,如今卻都站在妳這壹邊。”
二皇子擡起頭來,那張俊秀的面容裏夾著壹絲隱怒:“如果是本王能力不如妳倒也罷了,可是……這只不過是因為壹些很荒唐的理由,壹些前世的故事,而造成了如今的局面。如果父皇肯將監察院交給我,難道本王會做的比妳差?如果父皇肯將內庫交給我,難道本王就真沒有能力將國庫變得充裕起來?修大堤,妳我都不會修,妳我都只能出銀子……安之啊安之,妳不覺得很不公平嗎?畢竟我才是正牌的皇子。”
範閑沈默了許久,心知自己在慶國這光怪陸離的壹生,如今所能獲得的這種畸形權勢……全然是因為當年那個女人的遺澤,當然,那個女人也為自己帶來了無數的麻煩與兇險。二皇子所言,其實並非全無道理,若自己與他易地而處,自己不見得比他做的更好,二皇子不是沒有能力,而是壹直沒有施展能力的舞臺。
他緩緩說道:“世事從無如果二字。”
“不錯,所以妳如今左手監察院,右手內庫……”二皇子微微譏諷說道:“如此大的權勢,想來也只有當年令堂曾經擁有過……所以,妳現在提前開始怕了。”
範閑的面容再次僵了壹下。
二皇子平靜說道:“妳想過將來沒有?妳今日究竟是為誰辛苦為誰忙?”他眼光微轉,看了三皇子壹眼,笑道:“我皇室子弟,沒壹個是好相與的,妳自己也是其中壹屬,當然明白其中道理。”
三皇子低著頭,根本不敢插話。範閑知道老二並不是在危言聳聽,只是他有自己的打算與計劃。
二皇子淡淡說道:“妳是真的怕了……想壹想妳現在這孤臣快要往絕臣的路上走,日後不論是誰登基,這慶國怎麽容得下妳?怎麽容得下監察院?”
範閑平靜聽著。二皇子繼續說道:“妳之所以怕,是因為妳是聰明人,妳知道妳如今權勢雖然滔天,卻只是浮雲而已,甚至及不上壹張薄紙結實。”
二皇子嘆息著:“因為妳手頭的壹切權力,都是父皇給妳的,只需要壹道詔書,妳就可以被貶下凡塵,永世不得翻身……父皇雖然寵愛妳,但也不是沒有提防妳,這幾年任何路子都由著妳在闖,卻絕對不會讓妳染指軍隊,其中深意,想來不用我提醒。”
最後二皇子總結道:“正因為妳怕了,所以妳要……自削權柄!”
……
……
大皇子喝了壹口酒,冷漠地看著自己的兩個兄弟像兩只鬥雞壹樣說著話。
範閑沈默了很久,沒有接二皇子這句話,只是輕聲說道:“權力本是浮雲。這天下何曾有過不敗的將軍,不滅的大族?殿下是皇子,心在天下,我卻只是臣子,我要保我自身及家族康寧……”
二皇子截住他的話頭,冷冷說道:“本王知道,妳堂堂詩仙,向來不以皇室血脈為榮,反而刻意回避此點。但妳捫心自問,若不是妳厭惡的皇室血脈,妳豈能活到今日還能活的如此榮光?”
壹座四兄弟,二人沈默,二人對峙。
“放手吧。”二皇子誠懇說道:“妳的力量其實都是虛的。妳不敢殺本王,便只能眼看著壹天壹天地過去,而妳卻壹天壹天地危險。既然妳已經察覺到了這點,為什麽不幹脆放手的更徹底壹些?以妳在這天下的聲名,妳是婉兒的相公,妳是父皇的兒子,妳是北齊的座上客……誰會為難妳?誰敢冒著不必要的風險為難妳?靈兒說過,妳最喜歡周遊世界,那何必還困於這險惡京都,無法自拔?”
範閑的眉頭漸漸地皺了起來,手指頭緩緩捏弄著酒杯,開口說道:“殿下,先前便說過……我與妳的想法是壹樣的。”
他擡起頭來,面上容光壹湛,望著二皇子平靜說道:“壹年前在這樓子外的茶鋪裏就曾經說過,妳不放手,我便要打到妳放手,而且事實證明了,如今的我,有這個實力……茶鋪裏的八家將,妳再也看不到了,這就是很充分的證明。”
聽到茶鋪二字,二皇子面容頓時壹凝,想到了壹年多前的秋天,在抱月樓外茶鋪裏與範閑的那番對話。其時的對話,是發生在王爺與臣子之間,而壹年過去,範閑的權勢像吹氣球壹樣地膨脹起來,最關鍵的是,兩個人的真實身份也逐漸平齊了。
“我為何放手?”二皇子有些神經質地自嘲說道。
“殿下中了長公主的毒,我來替妳解。”範閑壹句不退,冷漠說道:“當初的話依然有效,殿下何時與長公主保持距離,真正放手,本官許妳……壹世平安。”
“妳憑什麽?”二皇子認真地看著範閑的眼睛,“難道就憑監察院和銀子?”
範閑搖搖頭,說道:“不憑什麽,只是我欠皇妃壹個人情,欠婉兒壹個承諾,今夜之事,殿下應該心中清楚,我便是要清空殿下私己的力量,將妳從這潭爛水裏打將出來。”
二皇子壹想到今夜自己所遭受的巨大損失,終於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那抹淒寒,陰怒說道:“為什麽是我?父皇不止我壹個兒子,妳也是!”
“我沒有壹絲野望,我只是壹位臣子。”範閑說道:“再過兩天,殿下便會知道我的誠意。至於其余的殿下,壹位是我的學生,我會把他打乖壹些,大殿下更喜歡喝酒,太子我不理會,只好針對您了……您說的對,這血脈總是值得尊重壹二的,所以我會盡壹切力量阻止那種可怕的事情發生。”
二皇子心頭壹寒。屏風有壹個縫隙沒有擋好,冬日裏的寒風開始在抱月樓內部緩緩飄蕩。範閑最後說道:“請殿下牢記壹點,陛下春秋正盛,不希望看見這種事情發生。”
熱門書評
-
時堇年2019-12-15
竟然還是免費的 萬歲 -
shagen2020-01-08
這本書放到這個專區不太合適 -
xb20020921064292020-02-11
喜歡! -
bitchloves2020-01-11
樓主辛苦了,謝謝樓主分享!!! -
放棄希望012020-01-10
樓主辛苦了,謝謝樓主分享!!! -
qinwanki20192020-01-06
感謝分享!還全部免費。